中佛协副会长纯一大和尚在京都净土宗总部佛教大学课题进展交流报告会上发言
来源:菩萨在线 发布者:妙音 时间:2014-06-01 
中佛协副会长纯一大和尚在京都净土宗总部佛教大学课题进展交流报告会上发言

京都净土宗总部佛教大学课题进展交流报告会

净土宗宗务总长和佛教大学校长以及相关大学的教授一同参加听取交流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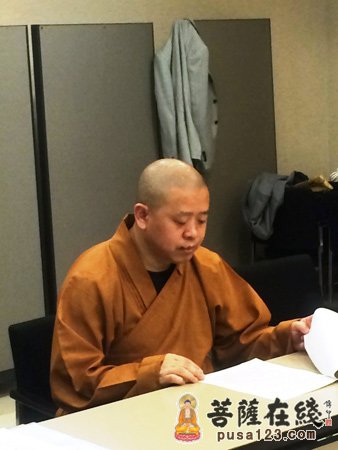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京都佛教大学客座研究员 纯一大和尚
菩萨在线海外讯 2014年5月30日,中日佛教书法交流史研究开题报告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京都佛教大学客座研究员纯一大和尚在京都净土宗总部佛教大学课题进展交流报告会上发言。净土宗宗务总长和佛教大学校长以及相关大学的教授一同参加听取交流成果。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自公元六世纪,佛教东传日本以来,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其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而这就意味着,日本佛教既带有中国佛教的普遍性特征,又蕴含了日本社会文化的民族性特征,这双重特征构成了研究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问题更是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研究学者对此的关注不断增多,各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是对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度和史料的挖掘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后,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佛经的记载和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书法伴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日本、韩国等地,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汉文佛教典籍成了重要的媒介,对汉字的文化心理反应,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之间也有共通之处。发展到今天,中国与日本的佛教书法都有着丰富的遗产和辉煌的历史,但是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日本佛教书法始终是在对中国佛教书法的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毕竟汉字是中国的,但是日本佛教书法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表现在作品上,还一点一滴的蕴含于整个书法发展的轨迹中,就如同是中日佛教的交流史一样。从微观角度,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有助于探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个别性差异,也有利于深入对佛教书法发展的研究。因此,本文选择对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定方向——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历程共经历了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几个阶段,这几个时期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叠的,相互对应的,日本同时期的佛教书法深深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种影响的表现。中国佛教书法植根于几千年一脉相承、内在结构体系较为完备的文化背景中,它不易受影响,也不易被破坏;而日本佛教书法则不同,它是一种开放式的,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随时调整自己的文化形象而发展的。在文化交流愈益频繁的今天,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日佛教由于同处在东亚文化的环流圈中,相似的文化背景促使双方交流频繁。而在这一交叉往复的过程中,日本书法尤其是各个时期的书法作品一一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书法行家的重视,这是中日佛教书法交流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直至今日,中日在佛教书法方面的交流一直在继续,虽然印刷术已经十分普及,但是抄经、写经的方式也从未中断,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因此十分普遍。由此看出,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探讨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中日佛教的交流或者书法艺术的交流都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中日佛教书法的交流还缺少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希望可以在更新观念、方法上加深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从多途径、多角度对中日佛教文化的相互影响加以分析探讨。
二、学术史回顾
(一)以中日佛教书法交流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成果
佛教的传播与书法的交流有着很大的渊源。自佛教传入日本后,手抄佛经也在日本渐渐普及,可以说,古代高僧大多是半个王羲之。僧侣和佛教徒在抄经的同时掌握了汉字的书写技巧,也成为第一批书法艺术的传播者。这一盛况,延续至今。日本人民在学习与移植中国书法的上,发展并创造了一种新的书写艺术——日本书道。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僧人、学者交流频繁,大量佛教书法和名帖碑迹的传入,促进了平安时代以“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书法家的诞生,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真正确立。宋代尚意书风的东传,更促进了日本第二次书法高潮的出现,以“禅宗墨迹”为代表,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最终成熟。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佛教书法交流一度中断,直至建国后又重新恢复,近年来渐有繁盛之势。与此同时,有关佛教书法的研究也开始兴起,这一方面的专著有李梅花著《十——十三世纪宋朝高丽日本文化交流研究》(华龄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版)叙述了以荣西、道元为代表的入宋僧,在回国后继承并发扬了“黄氏(黄庭坚)书风”,对日本墨迹书法产生的重要影响。胡建明著《宋代高僧墨迹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三月版)中分析了东传的宋代禅宗墨迹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及其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徐明利、董惠宁著《中日高僧书法选》(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选取了部分中日高僧的书法精选,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提供了直接的客观资料。
此外,涉及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研究成果的内容包括有:叶喆民著《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该文梳理了由唐中期至晚清中日两国书法的发展历程,尤其突出了禅僧,不仅有东渡日本的鉴真、兰蹊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隐元、即非等,还有来中留学的最澄、号称“三笔”的空海、荣西、道元等,为两个书法艺术和文化交流所做的重要贡献。周逸人著《中国佛教与日本书法艺术》(《内明》一九八八年第二〇〇期)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朝代在佛教书法方面的交流,并列举了不同时期日本来华求学的高僧,分析了他们在书法上的超高造诣。何鑫、付伟《由佛教写经看中日历史文化交流》(《江桥抗战及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下)》二〇〇四年)以佛教写经为入口,探讨历史上中日关系真实状况,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价值。何鑫著《中国佛教写经与日本书道》(《佛教文化》二〇〇九年第六期)重点论述了汉文佛教写经的产生与东传,日本书道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成熟,并相互交流的过程,对研究两国佛教书法交流有重要价值,也对研究日本书道的变迁提供了借鉴。李静著《浅析日本书道与中国书法的渊源及区别》(《兰州教育学院学报》二〇一二年第五期)以日本书道为切入点,探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其中佛教写经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陈健健著《禅与日本书法》(《青年文学家》二〇一四年第三期)以中国式佛教的典型——禅宗入手,比较系统地介绍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并对日本文化的诸多影响。尤其是平安时代的佛教写经和镰仓时代的禅林墨迹都是禅宗影响后的产物。总之,日本书法,自古以来受中国书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的禅宗的深刻影响,为研究两国的佛教书法交流提供了新的分析视点。
以同一视角进行分析论述的还有相关学位论文:
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二〇〇七年)以中国禅林中最具影响的高僧赴日传法为主线,即宋代高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赴日传去临济宗的纯粹禅法和尚意书风,并移植宋代禅宗丛林制度及宋代理学。此外论述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清拙正澄等元代禅僧赴日传法并带去元代大书法家赵孟叛、张即之等人的书风,对本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中日佛教交流史中涉及到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成果
佛教交流史一直是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课题,在论著中日关系时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在这一方面,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著有专论的是台湾的研究学者。释东初于一九七〇年编有《东初老人全集二·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东初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六月版)全面地描述了历史上中日关系交往,对佛教交流、高僧互往也有细致的分析论述,为研究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一个宏观背景。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八十一第九辑中日佛教关系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版)从各个方面对中日两国佛教交流的历史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中日佛教的未来做出了展望。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著《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华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版)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唐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来中日僧的社会活动及归国后对中文化的移植和影响。内地的研究时间较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中日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版)收录了两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内容,对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特点及中日佛教分别予以阐述,对研究中日佛教关系的发展提供不少借鉴。稻冈誓纯《日中佛教交往的一个侧面》(中国佛教协会文化研究所,一九九六年十月版)以赴中求法的圆仁、成寻二高僧为例,探讨其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及对日本佛教带来的重要影响,对研究中日佛教交流有所裨益。刘建著《佛教东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版)以佛教的传播为对象,以佛、法、僧为主体,研究佛教东渐的历史,进而分析各民族文化广泛交流的历史。
以特定时间段为研究对象的中日佛教交流论著有:
姚嶂剑著《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版)分析了唐代中日友好往来情况,并分析了日本学问僧、请益僧等求学归国后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变化及影响,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提供了阶段性的研究资料。陈继东《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版)以清末日本流传的几部佛教典籍为入口,分析中日两国在佛经刻印活动上的不同,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关系。郝祥满著《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二年六月版)通过来宋日僧奝然的个案研究,揭示唐末宋初佛教如何作为媒介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僧侣又是如何成为民间使节沟通两国关系的,以及中日彼此的文化自尊如何影响了相互之间政治关系的重建与发展。张丹桂《隋唐时期佛教东传日本之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二〇〇七年)主要分析了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探讨佛教之所以能在日本取得突破的原因,以及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及对日本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对研究佛教书法交流有所借鉴。
以某一特定人物为研究对象的中日佛教交流论著有:
王勇《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〇七年第五期》)主要研究了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广泛影响,他不仅开创了律宗列为“南都六宗”之一,还涉及书法、建筑、美术、工艺、医学等,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觉多《一山一宁禅师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和影响》(《佛学研究》二〇〇九年第一期)论述了一山一宁禅师以元朝使节身份赴日后为传播中国禅宗文化,恢复和推进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友好交往,并对日本的禅学、宋学、文学、书法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而得出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徐永红《鉴真东渡及对日贡献》(山东大学硕士论文二〇一一)主要对鉴真到达日本之后的对日贡献作出介绍。鉴真东渡后,在日本传授戒律,弘扬佛法,被誉为日本天台宗的先驱和律宗的祖师。鉴真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将建筑、雕塑、医药、绘画、书法、文学、语言、印刷、饮食等唐代先进的文化带到了日本,并无私地传授给日本人民,为推进日本的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对研究特定人物对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重要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研究中的有关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已有成果
书法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那么在研究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中是绝不能忽略的。僧人书法作为书法领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版)介绍了以“三笔”为代表的日本平安时期的书法家,在赴中的日本僧人影响下,书法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日本风格。榊莫山著《日本书法史》(陈振濂译,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版)阐述了日本书法史的诞生及转折,并分析了各时期的书法演变,而佛教书法作为日本书法的推动力在书中也有重要的描述,对研究各时期日本佛教书法的演变提供了有力支持。王勇、上原昭一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唐五代宋元时期日本书法之西渐,并就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展开分析,将中西方书法之间的交互作用体现的淋漓尽致,对我们研究佛教书法有极大裨益。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在日本》(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中华书局二〇〇二年四月版)对各时期中日书法交流盛况,分析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重要影响。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月版)以日本藏有的五百余件宋元禅僧墨迹为着入点,以临济宗杨岐山派僧为主,考察书法史上用印的缘起和意义所在。并通过对日藏宋元禅林墨迹的研究,了解日本书道的历程,并深入挖掘宋元书法家对日本书法艺术的影响。陈小法著《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一年二月版)本书以日僧的日记为主要文献依据,同时,追溯明代中日之间书籍交流的特点与方式。
关于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研究,学术界多有论文涉及:
朱卫新《日本书道与中日书法的文化交流》(《东亚北论坛》一九九八年第二期)以日本书道的诞生及发展,由小见大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并说明中国书法对日本书道的影响。吴冠玉著《中日书法的血缘关系与交流》(《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二〇〇三年第四期)叙述日本在学习汉字,并借鉴汉字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同时,他们在学习和移植中国书法时,也发展创造了本民族的书写艺术——日本书道,直至今日中国书法仍与日本书道交流频繁。尚荣著《僧人书法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二〇〇四年)重点分析阐述了僧人书法的历史演变,由原来从属于佛事活动、体现集体意志的行为转变为体现个人意趣的书法行为,从统一风格到多样化书风的历史,对研究中国佛教书法有着重要意义。陈华《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文史哲》二〇〇五年第三期)叙述唐至明清时期,中国书法家对日本书法界的影响。李攀《“书道”之道——日本书法和中国书法的渊源关系》(《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二〇一〇年第六期)同样探讨的是中国书法与日本书道的相互关系。张亮著《中国书法对日本书道的重要影响》(《美与时代》二〇一一年第九期)叙述日本在学习与移植中国书法的基础上诞生了日本书道,此后在各时期中国书法的影响下,日本书道的演变与发展。莫葸著《浅谈汉朝至宋朝时期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与意义》(《巴蜀艺术》二〇一三年二月)阐述了在汉朝至宋朝的一千四百余年中,中日书法交流的主要方面是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书法在中国的影响之下经过了唐风书法、国风书法两个阶段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书法样式——和风书法。旨在梳理汉至宋之间各个历史阶段中日书法交流的概况,并探求这种交流对文化发展的意义。这些成果都对我们研究中日佛教书法的交流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多为整体性的宏观研究,尤其是对中日佛教关系的研究更是如过江之鲫。而以中日佛教书法交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以学科交叉方法进行的研究甚少,综合性研究成果也不甚理想,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两国佛教书法交流的切入点。此外,研究的热点且多集中于两国的书法交流,对更细致地佛教书法交流则一语带过,并没有深入系统的分析成果出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近年来,区域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区域经济中微观、细化的素材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对中日两国的佛教书法交流也可以从这一方向入手。此前,已有部分作者关注这一点,但多以某个特定区域研究中日两国的佛教交流情况。如林正秋《南宋杭州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二〇〇〇年第二期)、吴平《民国时期上海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法音》二〇〇一年十一期)、林正秋《元代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史》(《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二〇〇二年第一期)、温金玉《玄中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法音》二〇〇二年第五期)等等,总之研究对象是越来越小,研究的深度、广度也逐渐增加。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一、文献的方法。本文研究的基础就是尽可能的收集中日佛教书法交流的相关高僧墨迹、资料、日记等等,以期在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再与论著中的材料和观点加以印证,然后再进行分析探究,有利于弥补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
第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佛教书法作为佛教和书法艺术两个不同领域的综合,其涉及面较广,需要结合美学、历史学、佛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知识展开研究。
第三、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方材料与日方材料进行对照使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始终错综复杂。虽然佛教书法的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也不能脱离整个时代背景的影响。对同一作品,可能中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要求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体现研究的客观性。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时间和佛教宗派的区分,如北宋中晚期至南宋灭亡的二百余年间,则为日本的镰仓时代,为日本的中世。更要注意不同宗派间的区别,如临济宗的杨歧派在传入日本后分为虎丘派和大慧派等。
论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学术史的相关回顾。
第二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七章,此为论文的主体。
主要介绍唐代以来,中国书法对日本书道的相互交流影响,日本书道由诞生、演变到成熟,并详细介绍了各时期在日本书法上有较高造诣的书法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日佛教书法的相互关系。
第三部分为本文总结。通过对中日两国佛教书法交流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得出其对中日两国的书法艺术、佛教传播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产生的诸多广泛影响。
目前,课题的初步框架和书稿已经完成,但还有许多资料和图片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希望在佛教大学的访问期间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也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填补中日佛教书法交流史的空白。
(责任编辑:范祖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