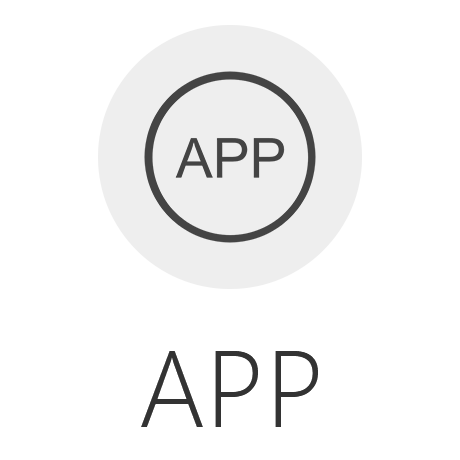金易明教授
大菩文化佛讯 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的“融摄”精神一向为国人所称道,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具有宽阔的文化胸怀的有力证据。由此,国人又常常因此而联想到西方的“异教徒”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长达二百馀年旷日持久的“十字军东征”,对西方人于信仰问题的固执并为此大动干戈,或嗤之以鼻,或一笑了之。但是,从文化接受的形态方面考察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接受状况,则由一个侧面深刻反映出中国佛子的对时代和主流文化的几乎出于本能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其实质是媚俗顺世。因为,其中所发生的事实已超越了文化交流现象中必然产生的融合互摄,也非比较宗教学意义上的教理嫁接和教规移植,而是中华文化形态对拥有异己性质的印度文化形态的无视其文化特质的强制改造,也是佛子们对本土文化形态的无原则苟合趋同。这一问题随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即相伴而至。其正面的功效是推动并促进和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使佛教这个纯属异质的宗教文化得以在儒学一统天下的中国找到其适合的生存土壤。
但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嬗变的过程中,也随之串味变质,当儒释道三家合一之风盛行时,正统的印度佛法面对强大的中国本土风俗和主流思想体系,则只能发“梅熟已过南岭雨,橘酸空待洞庭霜”之感歎了。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织,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玄奘大师一生即在为寻觅其真正印度佛学的“橘味”而不懈努力,但国人却久尝“织味”,而对“橘味”兴趣索然,于是,在为玄奘大师送上最美妙的颂词之后,将他的思想学说束之高阁,自赵宋以降,直至清末,寺院以经忏适应民俗,僧众以佛事迎合民众。即使论禅谈道,也流于文字般若,与文人的吟花弄雪般的无病呻吟同出一辙,缺乏宗教所应有的人文关怀,更无从谈宗教所必须拥有的神圣品质和终极关怀!
有幸的是,对此佛法日益式微的现象,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和佛教居士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予以具体分析,从源头上寻找解决的途径,即由对佛学基本文本的校勘和辨析入手,旨在还原释尊真意,阐述佛法基本原理,并从历史的纵向上和教理教义教规本身现状的横向上总结千馀年中国佛教流弊。其中,尤以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支那内学院派居士和学者贡献最著。特别是吕澂先生,他曾经就中国佛教所存在的导致佛法宗旨串味弊端,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抨击。其在《佛法与世间》的演讲之附识中指出:“今之谈佛法有三大病,若不及时对治,终必不可救药。三病者何?一曰泥迹,专讲婆诃苦恼、生死可畏一套话头,引人厌世躲闪,此从小乘出,却毫未学得小乘之严肃深刻精神,只剩有浑身的自私自利解数。此为一大病。次曰蹈空,专唱高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说得一片响,完全不著边际,反倒转来以涅槃菩提将就生死烦恼,由此引人向浮泛空虚,真同方广道人,于佛法却一无所得。此又为一大病。三曰纯任知解,无论说生道死,谈空论有,概从知解上理会,只图说得顺口动听,不管于自身受用如何,不问于他人利益如何,更不理会于此人世如何衔接得上,结果一场空话,竟与人生漠不关心。此又为一大病”。 此分析持之有故,立之有据,凡正视中国佛教历史,又有人格勇气直面现实者,当认可吕澂先生鞭辟入裡的分析。
吕澂先生毕生的佛学研究,其主旨在于为佛法正本清源。他的佛学贡献不仅表现在对佛学文本的校勘、伪经的辨析,以及对印度和中国、西藏佛学体系及其历史沿革的研究和整理方面,也不仅表现在他几十年如一日,以其深厚的佛学造诣结合天才般的语言功力,校勘出版了在学界和教界影响甚巨的《藏要》,编撰了《中华大藏经》的目录。笔者以为,他的学术活动以基础性的文本清理辨正为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佛学文本的清理辨正,发掘、寻觅已被历史长河所堙灭的释尊真意。因此,他通过自己所写的系列著作,表达了佛陀的本意,在貌似枯燥的学术论述中,展现了佛陀的本怀。其中,分别以《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为题的三篇论文,同时又以《佛法与世间》为题的演讲作辅翼,构成了佛学基本问题系列著作,虽在其整个著作体系中的分量并不重,但这三篇论文确乎是独步佛坛的孤明首发之力作。《正觉与出离》阐述了佛法修学的根本目的和途径,《缘起与实相》阐述了佛法的基本教理和学术宗旨,《观行与转依》阐述了佛法的基本修学方法和修学过程。所以,吕澂先生将上述三篇论文均冠以“佛学基本问题”的副题。其实,正如众所周知的是,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本非佛教入门教课本一样,以“佛学基本问题”为副题的上述三篇论文,也决非佛学基础知识读本,而是吕澂先生对佛学的基本、普遍、重要的教理、观念的精心整理和阐发,在吕澂先生的佛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代表意义。因此,本文仅在吕澂先生博大精深的佛学学术体系中,藉此三篇论文暨《佛法与世间》演讲所涉及的范围,阐发吕澂先生的佛学思想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