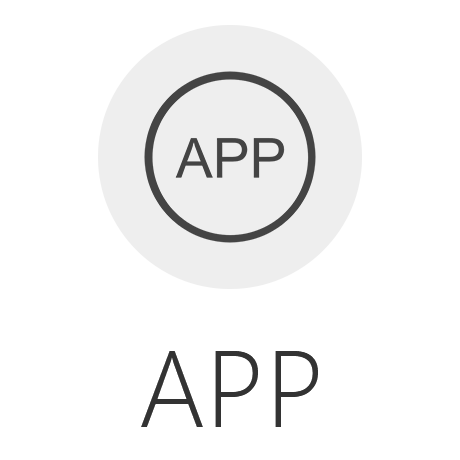专访全球首部佛陀经教电影
卷首语一:
有这么一个书生,他叫张迪。
他有着多重身份,既是电影导演,又是国学导师。
既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本科毕业的高材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生,
又是本焕学院佛教传播学专业讲师、佛教艺术与传播学专业教研组组长。
这些身份让他有着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独特气质。
而最令人惊叹的是,是他执导拍摄了一部史无前例的佛陀经教电影——《首楞严演义》。
卷首语二: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真人演绎的方式,将一部佛教经典拍成电影。带领观众回归佛陀住世的古印度,饱含浪漫的宗教情怀。
人生能有多少个第一次,这部影片的上映,堪称佛教文化传播史上的盛事,也堪为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这部影片于2017年4月24日在马来西亚内部首映成功之后,即将于5月3日“释迦牟尼佛圣诞日”之际,在福建宁德瑞迹寺举行中国大陆内部首映仪式。
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导演、编剧张迪老师,老师也在文殊菩萨圣诞日即将到来之际,带来了对所有歌友和读者们的真诚问候,感恩。
小编对话张迪老师
小编:您为什么会选择用电影的方式去演绎一部佛教经典?
导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首先,感恩中国福建省宁德瑞迹寺的住持法师——性龙上人,他是我愿依止的一位恩师。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办,归根结底,要溯源于性龙法师早在十几年前发下的一个大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召集一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制作者们,乃至各界社会资源,来共同将这部在“末法时代”关系到佛教兴衰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拍成电影,并以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直观的电影手法,来弘扬《楞严经》,为众生开启究竟无上的佛陀智慧,帮助新时代的修行者加深对经典的印象和理解,促进佛子早日破密开悟、永获正知正见!
在性龙法师刚开始发这个愿的时候,我还在经历着青春激荡的大学本科时代——据说,那是在2003年左右。后来,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尚还不成熟,性龙法师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化作现实。直到12年以后,在2015年的春天,我有幸结识了性龙法师,我跟法师一见如故,彼此感到志趣暗合、心意相通,于是感应道交,我便乘着法师的大愿,义无反顾的踏上了这段浪漫而多舛的圆梦之旅。
一切似乎早已注定,缘,实在妙不可言。
而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古往今来,人类在文化艺术上所创造出的成果、建树,常在宗教领域登峰造极——不管在哪一种宗教里,无论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还是诗歌、文学、戏剧等种种形式,都曾留下过永垂不朽的骇俗之作。这种种无可挑剔的宗教文艺作品,永远不随时代演进而衰没淘汰,不随时间推移而积毁殆尽,浓郁的宗教情怀和人文主义光芒耀眼,永不黯淡,永不褪色!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西斯廷教堂的穹顶、巴赫的交响弥撒、但丁的《神曲》、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古今中外,宗教文化艺术作品的经典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古往今来,博大精深的宗教艺术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宗教艺术里面,我们不仅能够深深感受到人类文明的滋养、文化艺术的熏陶,更能够从浓厚的宗教悲悯情怀和人文主义的光芒中,抚慰疲惫的灵魂、疗愈颓衰的心灵——那种浪漫,那种唯美——那简直是人生于世间最高雅的精神享受了。
你是否能够感同身受?
在世界各类宗教当中,佛教是我的个人信仰。佛教,虽说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舶来品,但它早已完美的融入中国的传统国学文化的血脉之中,儒、释、道三学,在我的心里,不分彼此,不分伯仲。而佛教艺术,随着佛教文化和信仰的传播历史,遍历沧桑聚变,万变又不离其宗,给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笔又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光辉永垂史册。仅举一例——敦煌艺术,这就足令我们顶礼膜拜,并终其一生进行研究、发掘、考证的了。
宗教艺术,向来是世界文化艺术巅峰水准的集大成者;中国佛教艺术,也曾走在时代的前列,也曾是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向导和生力军,也曾引领过中国古代国学文化的先进方向。从理想上来说,当今佛教艺术仍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巅峰水准的集大成者,引领时代潮流;可现实骨感得很,近现代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明显迟缓下来,弱化了自身的鲜明个性与特色,又难以摆脱中国封建文化的路径依赖;同时在生态上,也颇适应不了当下这个“急功近利、活色生香、虚实难辨、雅俗失格”的“互联网文化”时代了。
小编:您用电影演绎佛经,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导演:电影,是门综合的艺术形态,并依赖最前沿的数字媒体技术得以操作、实现。它正符合我上述的——“是各类艺术巅峰水准的集大成者”。
如果你有机会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就不难明显的感受到,那些挚爱电影并怀揣抱负的电影艺术青年学子,是将电影作为一种信仰而去追求的。我本人就是从“北京电影学院体系”中走出来的,电影,是我大学本科时代的专业,是我的老本行;当然,也无外乎是我会以之作为毕生追求的梦想之物。
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接地气的东西,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梦,更不是满足虚荣的把戏。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它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很多人生体悟、哲学思想、文化含量,乃至宗教信仰装藏进去;体量可以做到很大,内容可以高度凝练,关注焦点可以非常集中。它对我来说,是最完美的一种“文化容器”,我觉得这个形容十分恰当。
我在本焕学院佛教传播学教学的课程中,特别设立了“中外宗教电影研究”这一门课,详细讲解中外宗教电影的产生、发展、演变,并着重赏析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可悲的是,中国佛教电影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仅有的几部,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满篇缺憾;相比之下,西方宗教电影较为发达,多以基督教、天主教信仰或批判为题材或主题,而佛教的也少之又少。
站在佛弟子的立场上来看,这无疑是莫大的遗憾,唯发愿终己一生,填补这项学术、艺术空白。
从客观上来讲,电影作为一种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成长于二十世纪初,又在二十一世纪逐渐发展为“主流文化传播及意识形态输出的现代化综合艺术”,它博采众长,融合了其它各门类传统艺术于一身,又独具其超越传统的“逼真性”美学特征、“运动性”极强的视觉感官刺激效果,以及 “视觉”和 “听觉”双管齐下的多重震撼力;当下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并作为娱乐消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很典型的生活方式了。
佛陀经教电影《首楞严演义》中的一件重要道具——般剌密谛法师舍身东渡带来的“血渍经”
导演张迪(宝迪)在摄制现场,严格把关每一处工作细节
电影片名——首楞严演义
电影剧照——佛陀为阿难尊者摩顶受记,说大佛顶首楞严三昧之王
电影剧照——摩登伽无奈之下为女儿结坛作法,以先梵天咒术勾召尊者
而且,电影的传播效应很灵活,时效性强、话题性热烈,碎片化时间利用率高,特别能够跟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征契合。
如果从佛教传播学的角度来讲,众生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符号,最常用的器官莫过于眼睛和耳朵,佛教讲“眼根”和“耳根”,对应“眼识”和“耳识”,也就是视觉作用和听觉作用,用来攀缘心外的尘境。当然,立足于佛教修行来讲,这是不清净的习气,是凡夫众生依赖妄识的觉知分别作用,而产生的种种障碍修行、成佛的杂染之症。但是,一般的众生普遍如此,都免不了习惯于这种“执取色相、攀缘尘境,对号入座、沉溺于主观感受”的毛病。那么电影艺术,恰恰是迎合了众生惯于用眼耳等器官攀缘对境、又对号入座的导入于主观意识中产生“快乐、悲悯”或“恐惧、愤怒”等等情绪性的宣泄感受——电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高端前沿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现实生活及非现实生活“逼真性”的模拟,以传达作为作者的导演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主题。
那么观众通过对这些形式的主动或被动接受,在情绪宣泄的过程中,同时收获了艺术审美的滋养和思想文化的碰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电影和观众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觉得在这个新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用电影这种新手段来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宗教文化,是不二的选择。当然,更深刻的理由还远不止上述这些。
这也是我之所以能与性龙法师、果来法师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深度的默契,这种精准的共识,非是用语言文字能够准确形容概括的,它在我和法师的心中,由来已久焉!
小编:把佛经拍成电影,之前有过先例吗?
导演:我刚才说了,成功的佛教电影,总共也没有几部——当然,是因为电影还是一门很年轻的艺术,自诞生以来,飘摇不过百余年而已:把佛经拍成真人演绎的电影,更没有过,以往没有先例。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以往,有过很多将佛教故事、佛陀一生行教经历或关于佛教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的,或是将佛经制作成动漫影视作品的。但是将一部佛陀亲口宣说的经典,拍成真人表演的电影故事片,尚属首次。不仅在中国属首次,在世界范围来讲,也是首次。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多说两句。电影,是一个有特定规格的概念。我所指的电影,是在时长上、在工作流程上、在摄制规格上、在导演艺术上、表演艺术上、在后期制作的技术流程和行业标准上等等……综合来说,也就是——在视觉和听觉的呈现规格上,都要达到主流影院放映级的标准档次——这才叫电影。并不是随便制作几支网络“数码录像短片”就能叫做“电影”的,那样的作品,最高档次可美其名曰“微电影”,也就是传统所说的“短片”,而绝不能称作电影。
我这样讲,可能会伤害很多网络视频时代的作者、导演、制作人的自尊心;但请原谅,我必须扳正这个严肃的概念,我相信,会有很多电影业界同行会理解、支持我这番重点提示的。
我作为“北京电影学院体系”的一份子,作为一名佛教传播学的教师,我必须严正地指出这个问题,大家就当我是犯了“职业病”吧。
另外,从佛弟子的角度来说,我这样来发表意见,真无关“执着”,而确关乎“审美”——这就如同一个正信实修的佛弟子,看到有人举着“佛陀正法”的幌子,而尽行“相似佛法”、甚至“非法”之事,你作为佛子,能不严正指出问题所在吗?
“佛陀经教电影《首楞严演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或者说佛教文化传播史上,第一次以真人演绎的方式,综合运用电影艺术规律和技术手段,将一部大乘佛教经典《首楞严经》搬上了大银幕。”
——这是一段令我非常感动的评价,感恩出语者。
这无疑是第一次,是首创的一种电影布教的新类型,我们称之为“佛陀经教电影”。
小编:您在拍摄前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工作?
导演:筹备工作相当艰苦卓绝,甚至可以用“不堪回首”来形容。
因为这部经典实在太难了,不放下万缘而潜心深入研读,是无法真正搞懂这部“天书”的。我最初是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怀着“勇敢试一试”的精神,开始硬啃。我非常感恩福建宁德瑞迹寺的法师们、马来西亚尊胜佛学会的老师们,给了我那么多稀有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还有深圳本焕学院的同事法师们,给了我那么多及时的指点。在研读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培养着严谨治学的科研态度;在佛学院的工作环境中,我绵延滋养着浓厚的宗教情感。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理智和感性共存并举、严苛与浪漫相得益彰,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创作剧本过程中的思想、精神状态。
从具体操作上来说,我是“先译经,后剧作”——先把经典原文译作朗朗上口的现代汉语,又将这些现代汉语译文作为创作素材,逐渐融入故事,再慢慢加入情境感和行动性;再根据人物小传来组织情节,并依据我在初创时立下的导演阐述来时刻扳正主题思想;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断调整当下主流意形态和宗教立场之间的关系、尺度,既不能完全的将宗教信仰唯物化,又要严防宗教信仰出现极端、偏执的倾向,绝不可以出现意识形态的偏差……
具体的操作细节非常复杂,不是一般的宗教专家或一般的剧作家可以从单方面来解决问题的。那是一个自我斗争极其激烈的过程,非常不可思议。我对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现在却难以用语言来概括形容,因为太复杂了。
总结来说,首先,我是严格按照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来时刻调节电影主题思想和表达尺度的,丝毫不敢越轨,丝毫不敢偏执;并按照佛教文化、艺术、信仰“中国化”的要求,来精确、细微的调整印度美学和中国美学的比例,直至逐渐找到了平衡。毕竟,这部影片是我们中国的佛弟子们,在“自主、自办”原则的基础上,在“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时代背景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结合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积极、有益的部分;“白手起家、自己动手”,毫无依赖境外势力,依靠着坚韧的民族精神、十足的中国文化自信,和科学、正信的佛教信仰之力,通过团结协作,一点一滴的不懈努力,所创造出的一部“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贴近人民群众”的佛教电影文化艺术作品。
宗教电影的实质,应该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一种,倡导科学、正信,服务社会的文化艺术作品。
我很清楚,这部影片的佛教属性大于电影属性;义理属性重于叙事属性;如何科学而通俗的阐明《楞严经》中大乘佛教的精华义理,是创作的核心、要关、重中之重。在创作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楞严经》以外的佛教经论作品,以及爱因斯坦、霍金体系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参考书籍。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尝试,把抽象的理论具象化,把具象的感觉电影视觉化,再将视觉效果听觉化……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的这些过程,基本是同时进行的,有时感觉自己近乎人格分裂,眼睛的视力也从原先的200多度,逐渐蜕化到800多度;每每攻克小小难题的成功喜悦,伴随着身体不适带来的沉痛、沮丧;家人的精神支持,伴随着对我这种生活状态的极度无奈……所以说,确实是不堪回首。
初稿,用了三个月时间;二稿,完全推翻重来,又三个月;三稿,大刀阔斧,数易其稿,又三个月。到了临开机的前三天,没有合眼,最终将剧组统一工作用的拍摄本整理完成。别忘了,在上述这些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事无巨细的前期筹备工作——搭建主创班底,逐个游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为拍摄资金还没有着落,又不能妄语骗人,只能夹紧尾巴,顺情说好话,尽量在自己人格底线之上恳求大家帮忙,却往往在人格、尊严底线之上下无规律的浮动。
看景选景,带主创团队奔波,生怕大家不高兴,衣食住行,每个人都要舒适,才得以心安。因为最初我们没有合适的制片人,所以难免会出现很多人事上的问题;后来因为没有钱,因此又错过了与很多业界大咖合作的机会。但是瑞迹寺的法师们一直鼓励我、支持我,不断给我信心,我也坚信,弘扬《楞严经》是这个时代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诸佛菩萨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件事做好;更何况,我曾为了临场制止某次口舌争执而发过毒誓:“如果拍不好,我就下地狱!”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好在我已交出了大家普遍满意的答卷。
小编:你如此发心拍这部电影,最终是为了什么?
导演:楞严兴,佛法兴;楞严灭,佛法灭。弘宗演教,别无他求。
小编: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影片的大概剧情吗?
导演:这次完成的是《首楞严演义》的第一部,内容参阅《楞严经》原典卷一。当然,电影中实际的内容不止这些。
小编: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您希望他们关注哪些方面的东西?
导演:我不喜欢剧透,实在感兴趣的话就请花时间认真观摩,用心感受。
不妨着重看一看那些经典原文以外的种种文化含量和信息符号,例如:唐中宗元年广州制止寺的译经场是什么样子,四位翻译此经的大德——般剌密谛法师、弥伽释迦法师、怀迪法师、房融居士,以及同在译场的九位笔受法师,他们工作的流程是怎样的,译经场的规矩是怎么行起来的。
再例如:摩登伽家,母女二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历史上将她们定案为“婬女娼妓”;她们有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要不要根据历史的考证来给她们“翻案”;娑毗迦罗先焚天咒的来历,以及作为民间文化的咒术形式是怎样施展的。
又例如:波斯匿王宫和祇桓精舍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氛围?佛陀和圣众弟子们在祇桓精舍中的位置关系是怎样排座的?佛陀是一个高高在上、凌驾群众的“封建统治者”形象,还是一个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亲民教主形象?
再如对很多历史细节的电影化表现:“血渍经”是怎样藏在般剌密谛法师臂中的?用人乳清洗经卷的过程是怎样操作的?佛陀每次放光现瑞,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现象有没有物理学的依据?我们应该着重理解他表法的义理,还是满足于着相的浅层认识……等等,等等,很多有趣的问题。
诸多有待于观众从电影中发现、读解的细节,都是《楞严经》原典文里不曾有的,是大量考证来的历史文化信息,非常有意思。再例如:你知道什么是“译场八备”吗?你听说过“达瓦达西”吗?真的很有趣。这些,只能等你坐在大银幕前,仔细观察,用心感受,看完以后还要继续查阅、考证、学习,才能体会到无尽的乐趣。那是一种文化的滋养,也可以是一种揭秘的快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这样形容。
性龙法师与张迪导演:“有图有真相”的第二次“拉钩儿”——无言的承诺
电影剧照——文殊师利菩萨带领阿难尊者及摩登伽母女,一同返回祇桓精舍
电影摄影、灯光、录音组成员,在酷热的工作现场,坚持专注的工作
《首楞严演义》发起者、出品人——福建宁德瑞迹寺主持性龙法师
2017年4月24日,马来西亚《首楞严演义》全球内部首映现场,三场放映,场场座无虚席
小编:影片大概筹备了多少时间?
导演:前期筹备近一年之久,拍摄在一个月之内,后期工程七个月左右;再加上最初的酝酿、论证和案头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
我是2015年的4、5月份,接到的这个任务。当时性龙法师带领德一法师和随行的居士,专程到深圳跟我碰面,我非常感动。性龙法师的为人低调、关怀他人、幽默豁达、隐忍坚韧,种种美德都感召着我随之一起努力奋斗。当时在深圳,我跟性龙法师用小拇指“拉了钩儿”,再用大拇指彼此一按,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承诺,我必须完成。
后来八月初,去瑞迹寺实地考察,我发现实际情况非常有限,操作一部电影实在很难,恐怕不成。可是那次,又跟师父拉了一次钩儿——有图有真相。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想过放弃。
接下来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很多事情不方便讲,也没有必要讲了,无非人事,我还是选择遗忘掉吧。再后来,非常感恩中国传媒大学叶怀阳老师的加盟,她作为制片人,鼎力支持;非常感恩制片主任吕欣翰师兄以及他的团队,都是经验丰富、尊重行业的好兄弟姐妹们;非常感恩我的同学郑罗茜(饰摩登伽)、孟宇(饰房融),老朋友孙博(饰般剌密谛)、凤翔(饰弄臣)、周玉华(饰波斯匿王)老师,新朋友王千予(饰钵吉蹄)等等,还有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宏博法师(饰怀迪);当然,还有重量级的果来法师(饰佛陀)和桑吉平措(饰阿难)先生。要感恩的人太多了,莫说几千几万字,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提示:请大家坚持看完片尾字幕,看看“联合出品人”一栏,那近5000位为了真心弘法利生而布施、捐献出真金白银功德主们,无尽感怀!我特意在片尾音乐部分安排了“楞严咒心”的念诵共修环节,愿观摩影片的所有人一起持诵,回向给所有为影片默默付出的演职人员及一切众生,愿所有人福慧增长、早证菩提!
你们现在采访我一个人,要知道,我代表的是成千上万个人,我在此仅仅是大家的代言人而已。由我来代言,讲一讲大家的故事,讲一讲大家的愿力,讲一讲大家共同付出的努力。说着、说着,很多记忆犹新的细节又浮现在脑海了,唏嘘,感慨……
小编:电影拍摄地点选择在哪里?
导演:剧本中设置的规定情境有很多,实际拍摄的场景主要有四处:福建宁德瑞迹寺、洋中镇坂头村、西双版纳曼听公园,还有一处曼听宝佛寺。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无法自由的建造场景,只能在大体结构合适的场景中稍加改造,发挥美术师、置景师、陈设师、道具师的审美和经验,化腐朽为神奇,将差不多的结构改造成相对真实、完美的场景。
唐中宗元年制止寺的场景都是在瑞迹寺改造的,摩登伽家以及古印度村落的场景,是在坂头村——那真是神来之笔,贵在导演执拗的坚持;王宫、祇桓精舍以及其他佛陀时代的古印度场景,都是在西双版纳完成的。
小编:在拍摄期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导演:我们是2016年8月3日开机的,28号顺利杀青;除去从宁德到西双版纳大转场消耗掉的5天时间,实际拍摄只用了21天——还要除去反复无常的雨天造成的拍摄停滞。
不下雨的时候,气温四十多度,大家全部晒伤,盼着天气凉快一些;可是一下雨,凉快倒是凉快了,可是那就拍不成了,只能忍气吞声的等雨停。我每天都想跟老天爷谈判,可是哪有可能呢,只能仰仗信仰之力、心性之力,全剧组上下,团结一心,默默祈祷,共同克服种种困难。实际的困难远不止天气变化,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谈也罢。
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忍的人,但我每天看着大家要么是汗水湿透了衣服,要么是大雨浇透了衣服,没有一天是舒适自在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我在现场作为导演,除了有益于拍摄的话要一次次的啰嗦,其他时间我常是沉默不语的,主要是因为我看着大家一起受罪,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因难过而说不出多余的话来。
可是想想,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弘扬《楞严经》这部正法眼藏而一起受这份罪的,我想佛菩萨会领情的;再想想,未来有可能持续利益无量众生了解《楞严经》、学习《楞严经》、读懂《楞严经》,并有可能引领他们因此而走向开悟、解脱的自在人生,就立刻觉得一切都值得——尽管身体还是倍感煎熬,但精神却可以充实、愉悦的。
作为教师,我愿意分享一些切身的感受给大家参考;但是作为电影人,我很不喜欢分享所谓“艰苦的回忆”。因为干这行,受罪是正常的。祖师爷说“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很有道理。但我认为这种境界也太低了,“人后受罪”并不都是为了“人前显贵”——艺术家往往甘于窘困、甘于寂寞,倾其所能去创造出遗飨后世的唯美和价值,那必然是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更何况一部关乎宗教、关乎信仰、关乎佛教兴衰的大佛顶首楞严经教电影!
好吧,我们确实在用生命创造出了这部作品。虽然都还活着,但是身心疲惫、心力交瘁,约健康确是损伤了不少。没关系,来日方长,继续坚持!
小编:首映是在马来西亚举行的,效果怎么样?
导演:效果可以说非常好,很欣慰。
很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滚滚热泪。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只看到开场序幕的几分钟时,就已经泪奔了;之后每每看到唯美动情、或感受到导演在用心表达之处时,其感动总是化作泪水——这便是浓重而热烈的宗教情怀、信仰之力、心性之力的加持、感染作用!
如果你对观众是真诚、负责的,观众自然会给你彼此同样的反馈。我坚信这一点。虽然我们条件有限、困难重重,但是,在现有的资金体量和现实情况下,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的效果了。
小编:这样的反馈,除了欢喜,您还有怎样的感受呢?
导演:“悲欣交集”——用手捂着良心说,我们终于完成了。
尚有遗憾,但绝无愧欠。
小编:未来您还会不会继续将佛教经典演绎成电影呢?
导演:看客观条件允不允许,看自己身体情况吃不吃得消,看众生对经教电影还需不需要。
呜呼,一部全本《首楞严经》十卷,目前仅是用两年时间拍完了第一卷的内容。若要将全本十卷完整演绎成经教电影,还需要近二十年的时间。
不禁想起我人生中的一位重要导师、已故台湾戏剧泰斗李国修先生在世时常说的那句名言——
“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
在岁月成长中,我渐渐get到了。
卷末语:
感谢张迪导演和团队为弘法利生做出的伟大贡献!佛弟子一定要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将功德回向给更多的人!
真心希望更多人能关注、了解这部来之不易的佛陀经教电影,愿更多人能向宁德瑞迹寺恭请《首楞严演义》这部影片,并多多组织以“非盈利性经典教学为目的”的内部观摩放映活动。
附人物简介:
张迪,戏剧、电影导演,佛教传播学、国学导师,佛陀经教电影开创者,戏剧表演家、剧作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生,现任本焕佛学院传播学专业讲师、佛教传播与艺术专业教研组组长。
主打课程:《佛教传播学》、《佛教布教法》、《楞严经新译》、《资治通鉴全本精读》等。代表作品:佛陀经教电影《首楞严演义》、经典舞台剧《何惧良辰梦醒处》、《三人行不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