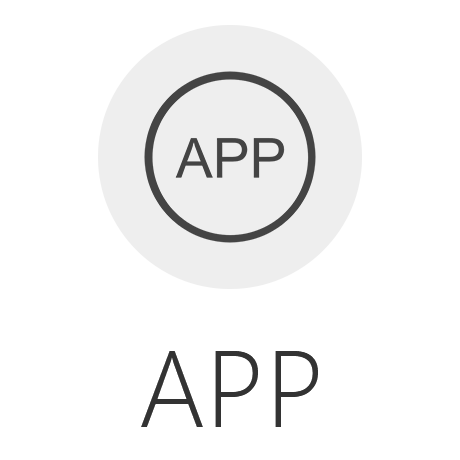韩敏先生旧影
2023年6月13日,上海书画研究院院长、海派著名画家韩敏奉安奠仪在杭州举行。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正慈法师曾于上海龙华古寺与其结下不解之缘;此次缅怀活动,正慈法师参与主法,并作文回忆了与韩敏老师昔日交往的点点滴滴,纪念这段忘年之情。全文如下:
乘坐上海回武汉返程的高铁,已经是晚间八点左右,再辗转坐在返程回黄石慈光精舍的车上,我一路回顾着6月13日,在杭州举行的,深切缅怀海派著名画家韩敏老师的奉安奠仪。有幸参加主法,让我再一次深感与老爷子的缘分。独自坐在车里,这一路上,老人家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萦怀不去。
老人家是2022年12月26日去世的,享年94岁。他是沪上知名画家,幼承庭训,醉心翰墨,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系上海书画研究院院长。他创作的《白毛女》《郑板桥》《林家铺子》《焦裕禄》等50多部连环画,是连环画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我因龙华古寺照诚大和尚的原因,与韩老师多有缘分上的相聚。记得当时看到了韩老师逝去的消息,就准备动笔,想着写下一篇短文,以此来表达我对韩老爷子的怀念,当时不知何故,把这件事儿搁置了。没有想到,缘分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同学普正法师,正是因为他的提前预知告诉了我时间,我就可以很从容地错开其他活动,安心地参加纪念韩老爷子的活动之事。


上了这个高龄的老人,离开人世可以说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老人家离开之后,我还是觉得没有亲近够。当时其实我也听说老人家阳了的情况,但是在我的心里头,总觉得他会好起来的,不会走得这么快。现实生活中的人世间,就是这样的变化无常,对于我们想亲近的老人家,总觉得他是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也让我们对这些老人的过世,产生了更多的念叨,还有深深的怀念。
回顾过去与韩老爷子的交往,始终与龙华古寺、与我们的照诚大和尚,密不可分。我曾经在龙华古寺,见证了照诚大和尚和韩老师之间的忘年交。
印象当中,第一次见到韩老师是在大连,照诚大和尚在那里举行一个大的慈善拍卖会。当时在一个很雅致、很宽敞的一位信众的书房里,韩老师在为大家写字,赠送给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韩老师。我也沾大家的光,也凑上去请韩老师给我题了一两幅字。韩老师那个时候,虽然说已经七八十岁了,但看起来很健朗,看身高个子年轻的时候肯定很高大。
后来我陪普正法师一起去龙华古寺的时候,基本都能见到韩老师。韩老师曾寓居于龙华古寺一隅“塔影院”“与翠竹流莺相伴,以丹青笔墨寄情”。龙华古寺里的韩老师,不是写字就是画画。因为年龄的关系,我跟他的沟通不是非常的多,他的言语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他说话夹带点上海话,我听起来是有一点困难的。
他比较随和,性格也很开朗。跟这个老人在一起也蛮亲切。渐渐熟悉之后,老人家很有意思,看到我们几个,看到我,普正法师,清远法师,有的时候他亦会主动问我们说:“你要写什么呀,我给你写呀!”很慈祥的一个老人。因为大家后来都熟悉了,气氛非常好,我们也就不避讳了,有时候我就请韩老师给我写四个字,或者请韩老师给我写一副对联,我们都很开心。
看得出来,龙华古寺的师父们对韩老师,尤其是照诚大和尚对老人家,对韩老师的这种尊敬和敬爱,真是像对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样。安排周到的接送,陪老人家在庙里一起吃斋饭,老人真的是过得很开心的,我看照诚大和尚也很开心。
每次龙华古寺的慈善义拍,作品基本是以照诚大和尚的字和韩老的画为主,有的作品还是他们合作共同完成的。每次义拍最少都是几百万元捐献给慈善基金会。前前后后也有近十次吧,这些年我也是见证者之一。韩老师总是很开心。他也会出现在拍卖会的现场上亮相,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每次拍卖都很火爆,效果都很好。
我突然想到,历朝历代如刘勰、苏东坡等好多些个文人,与僧人与道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一种不解之缘。韩老师与照诚大和尚之间的这种情谊,这种书画的因缘,是不是也类似于传统的文人与寺庙,与佛教高僧之间的交往情谊。韩老师曾寓居龙华古寺,他愿意续这么一段佳话,每思及此,都能感觉到是充满着雅趣的。佛教与文艺之间,有如照诚大和尚与韩老师,也是一件值得学习效仿,亦是值得称道的文化雅事。
出家人的气质,寺庙的清雅环境,这种气场气象,也蛮适合文化人的。而文人骨子里的清高脱俗的风骨,正好与寺庙也相契,一些个文化人也在影响着出家僧人。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在,写诗、写书法、绘画的,出家人像八大山人,当代也有一些诗画僧人,他们的相互影响都是正面的,都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的相互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值得去继承和发扬的一种影响力,也是值得佛教界和文化界关注的一个现象。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人与一个社会,一种生态之间,互相去包容,互相去兼容的必要性、必然性。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因为彼此都有需求。寺院有清静的环境,没有太多世俗的纠缠,文人们正好也在红尘当中,难得固有一份安宁心境。清净的道场,也需要有一份生活的清趣,一份接地气的层面。这是一种互补的文化,也是一种互需的文化。

回忆起来,还有一件趣而雅的故事。2019年的夏天,我与普正法师、清远法师作客上海龙华寺,照诚大和尚陪同我们一行拜访韩老师。其间,照诚大和尚介绍我是黄冈五祖寺住持。韩老师一时兴起,现场即诵北宋文学家王禹偁之作《黄冈竹楼记》: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新旧岁之交,即除夕。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韩老师此时已耄耋之年,却对《黄冈竹楼记》熟记于心,举座惊叹!后韩老师欣然为《黄冈竹楼记》作画,一高人逸士倚竹而立,一石几之上,一壶一炉一书,令人观之忘尘。照诚大和尚突发妙思,邀众人一起于画作上书写《黄冈竹楼记》之文字。当时照诚大和尚与普正法师、清远法师等一人书写一句,唯留首末两段又由我带回黄冈五祖寺,邀法师及书家完成。申鄂两地法师、文人遥遥以书会友,遂成书画双美之逸事。席间有黄石名士李声高先生作《题画记》并序:
己亥盛夏,正慈方丈邀聚,为上海韩翁所画“黄冈竹楼记”题字。余幸与会,目盲而未题。归寓后记之为诗,曰:
精舍朋侪会,题画竹楼记。
韩翁画竹楼,题款聚众艺。
高僧邀高人,高人逞高技。
灵犀贯古今,书画联珠璧。
竹楼不复存,文存留记忆。
依文夏为图,图存楼屹立。
世事有无间,存亡皆适意。
道立道无形,欲舍还无弃。
众手画葫芦,一人一天地。
助兴弄古琴,琴声断还继。
当年,我也曾经说过,要有可能请韩老师到黄冈来一游。可老人毕竟这么大岁数,他出来,我们也不敢擅自做主。但我是真心诚意想邀请老人家来黄冈一游的。可惜,心愿未了,老人家已经仙去。
老人家灵骨奉安日,我受邀主法,将龙华堂上事先备好的法语郑重而道:
时维公元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岁次癸卯四月二十六,先亡韩公敏老菩萨灵骨奉安,佛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今日老菩萨脱离火宅苦海,自在清凉,即今奉安一句又做吗道哪?
河沙尘世界,
何处是家乡?
浦水共西子,
心光印墨光。
时照诚大和尚慨然叹曰:“尘归尘来土归土,今日青山我作主!”他拄杖一跺:“安!”
顺便摘录照诚大和尚曾经发给我的,数首为老人家作的悼亡诗,如:
今天是敏公往生三七忌辰,寒风凛冽,雨雪交加,悲思无限!
雪雨悲伤别,
寒风解我哀,
禅缘情义绝,
泪湿戒香台!
癸卯上元,时值敏公六七忌辰。依调《长相思》,权作心香一瓣,用申思念!
迎新年,
又新年,
皓月圆时人未圆,
春归夜不眠。
礼佛篇,
画佛篇,
泪眼望穿墨海天,
来生再续缘!
癸卯正月二十二,敏公往生七七忌辰,一瓣心香,以寄苦思!
泪眼何人知我痛?
卅年亦父亦师亲。
禅关忆梦追欣悦,
墨海观心悟本真。
三友不全留雅契,
四时孤独隔仙尘。
奈何桥畔遥挥手,
百世千生此果因!
一字一句,皆是深心。禅缘墨缘,遥见三生。照诚大和尚与老人家的因缘,生死之间这种忘年之交,我想还真是少有,也让人蛮羡慕蛮赞叹,蛮随喜的。“百世千生此果因”,而今,老人家已“尘归尘来土归土”,却也幸,“今日青山我作主”!
今日我的心里,老人家依然萦怀,今日吾心,老人家作主!见青山,是老人家;观故墨,是老人家;读旧文,是老人家……(图文/正慈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