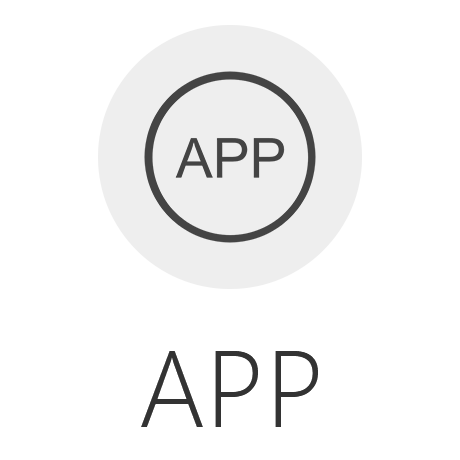佛教信仰大致可分为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的三种类型:一是僧团佛教,二是居士佛教,三是民间佛教或民俗佛教。原始佛教推崇的是僧团佛教,大乘佛教非常重视居士佛教的作用。中国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体,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海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僧团佛教,对居士佛教,日本有一些论文和少量的研究著作,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少量论文为主,有些佛教史著作中也有涉及,但很分散。显而易见,这些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基于科学方法的对居士佛教系统、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一直缺乏。潘桂明教授作为相应的国家基金项目终期成果《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以下简称潘著)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居士佛教研究通史性著作,丰富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补充了一般佛教史研究之不足,同时,也成为中国居士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这部作品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揭示了居士和居士佛教的内涵。
对于居士佛教的概念,人们已经朗朗上口,不过对于这一概念还有不同看法,特别在僧界并不缺乏反对这一提法的声音,认为如果居士佛教这一概念可以成立,那么比丘佛教、比丘尼佛教等提法也应该成立,而这样的划分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同时,僧伽的概念,广义上说,也包括在家众。其实从学理的角度看,与居士佛教相对应的,是由出家的僧人构成的僧团佛教(潘著称为“寺院佛教”或“僧侣佛教”),僧团拥有固定的寺院,掌握寺院经济,遵守严格的戒律,诠解佛教经典,对于佛教起着“住持”作用。从狭义上讲,僧伽的组成是僧尼。潘著开篇就解释居士佛教概念,这首先是因为居士的存在。一般而言,在家信徒都可以称居士。在对居士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潘著提出了自己对居士的解释,即:在佛教史中起重要作用的居士,实际上是“在家信徒中较为富裕、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第4页)。这部分人被称为佛教居士的主体,他们是在佛教史上留下“痕迹”的。当然,在家居士中还包括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较低甚至缺失、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贫穷的其他信众,这一类佛教信众,其中有一部分也可以归入民间佛教信仰一类。也就是说,民间佛教信仰和居士佛教信仰有重合的部分。潘著中涉及较多的是这一“主体”类型,也兼涉民间佛教信仰。在此分析基础上,潘著提出了对居士佛教的界定,指谓“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活动”(第4页)。在教理上,潘著对大乘居士佛教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将其归结为菩萨、菩萨精神和菩萨修行等方面(第14页)。这些界定为居士佛教提供了理论的证明。
第二,梳理了居士佛教的经典。
居士佛教的经典,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中都有,主要集中在大乘佛教经典中。潘著对这类经典所体现的居士佛教思想作了扼要的梳理,主要的内容包括:《阿含经》中的居士佛教思想,特别是其中所含的对居士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的记录;《华严经》之《净行品》反映的在家教团状况及居士的理想修行、《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所参居士体现的居士之地位;《法华经》的会三归一说、观世音菩萨信仰、诸法实相思想等所体现的居士佛教精神;《维摩诘经》由维摩诘体现的居士形象及宣说的居士佛教思想;《胜鬘经》的三乘归一乘说、如来藏说;《金光明经》的国王护法思想。当然这种分析还可以更详尽,但这不是此书的职责了。由此分析,潘著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特定的意义上说,全部大乘佛教几乎均以居士佛教为纽带……居士佛教的命运几乎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命运。”(第19页)这一结论足以显示居士佛教在大乘佛教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揭示了中国居士佛教的不同历史表现形态。
全书对于中国居士佛教不同历史表现形态的分析,概括为发端期(东汉三国时期)、滋长期(两晋时期)、壮大期(南北朝时期)、繁荣期(隋唐五代时期)、全盛期(两宋时期)、以三教融合为特点的演进期(辽金元时期)、反省期(明代)、维系期(清代)、改革期(近代)。全书十二章的安排就是基于这种历史特点的分析。这种不同特点的概括反映了作者对居士佛教兴衰过程及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
第四,展现了居士佛教的活动或作用方式。
作者将中国居士分为上层居士和基层居士两大类。上层居士以知识阶层为核心,包括东晋南朝贵族、名士、隐士,隋唐官僚、士子,宋明文人、士大夫,清末各类学者。基层居士指普通的信众,而这类基层信众中其实也有社会身份的重大区别: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底层,且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历史上常被诬称为“愚夫愚父”;有的是社会权贵阶层,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贵族“夫人”们也不见得有多少“文化”。又将居士佛教的展开概括为两条途径:一是知识型、理智型的,以贵族、官僚、士大夫为代表;二是福田型、情感型的,以普通百姓、社会民众为代表(第264页)。第二类的居士佛教发展,实际上指向了民间佛教或民俗佛教。
这两类居士的活动或作用方式有区别,作者对此加以细致的叙述。由此可以大致了解到,隋唐之前,上层居士往往表现为建寺造像(如笮融、晋司马氏等)、护法(如牟子、何充、谢镇之、刘勰、宗炳、颜延之、刘少府、罗含等)、译经(如支谦、聂道真父子、竺叔兰等)、诵经、交僧(这两者都是普遍的方式)、以文学艺术方式传播佛教(如戴逵、顾恺之长于佛画)、抄经(如萧子良等)、著述(众多的知识型、思想型居士留下了思想记录),等等。实际上以护法、著述对佛教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隋唐时期居士佛教的特点,作者专门概括出四点,即:通过撰写碑铭、塔铭、记、赞等宣传高僧的学问道德,弘扬佛教的出世精神;参与译经事业,担当重要角色;与禅僧打成一片,共同发明旨趣,促进文化繁荣;直接参加护教弘法的各项活动。两宋时期,特别表现为交僧参禅和净土结社,其中又以参禅为主要方式,由此形成独特的“士大夫禅学”,作者特别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历史作用加以讨论,这从一个侧面透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辽金元时期,主要表现为以学术促进三教融合思想的发展。到了明代,则表现为对佛教发展反省基础上的改革努力,晚明的居士佛教则以参禅为主要方式。近代居士佛教以文化学术和佛教改革活动为重要方式。
基层居士佛教的活动和作用方式,一般表现为诵经写经、念佛拜佛、斋会(盂兰盆会、忏法行仪等)、造像建塔,等等。隋唐时期,通过行香、俗讲、变文等形式促进民间佛教的发展。宋代常行净土结社,明清两代则更多地表现为念佛,这也和禅宗的衰落和净土宗的兴盛相关。潘著特别讨论了基层居士佛教信仰的基本形式。认为这种信仰形式在隋唐之前流行观音信仰和净土信仰(包括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唐代发展出地藏信仰。明清时期发展出和净土信仰并重的以四大名山为代表的四大菩萨的信仰。对于四大名山的信仰,作者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它维系了居士佛教的表面的繁荣,促进了民间佛教、民俗佛教的发展,但在事实上导致佛教陷入困境,“蒙受了在教义推广、思想展开方面的重大损失。”(第824页)这种评价也是该书的创新观点之一,这也反映作者对居士佛教的评价比较注重教义、思想的发展。
第五,分析了帝王对佛教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居士佛教的影响。
中国佛教之政教关系,特别表现为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这关系到佛教的兴衰。帝王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崇奉、扶持佛教,二是佞佛,三是限制佛教,毁佛或灭佛。一般的佛教通史也关注这一点,但作为居士佛教史,潘著特别强调这些态度对居士佛教的重大影响。比如第一类的表现及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是汉明帝感梦求法,作者认为,“明帝奉佛事件的本身,则为尔后居士的护法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依据”(第49页)。楚王刘英对于佛教的理解,将其视为同于黄老,所以将佛陀与黄老同祀,作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早期接近方式,也对“尔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带来深刻影响”(第51页)。东晋佛教的滋长,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帝王的提倡和支持有关,在玄学和般若学、名士和名僧互动的背景下,佛教通过帝王的支持扩大其影响。后秦姚兴支持鸠摩罗什译经,使得罗什译场不但译出了大量经论,也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佛学人才,从此,居士们“竞以知识僧侣为师,形成文化思想和理论思维研讨、传授的新格局”(第129页),对后世中国佛学和传统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第二类的表现及影响。佞佛的帝王,如南朝梁武帝,作者认为,他“是南朝居士佛教运动的一面旗帜,代表着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第191页)并从奉佛活动、佛学见解、三教态度三个方面分析证明这一点。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对梁武帝佛学思想的一种重新认定。第三类的表现及影响,作者认为,灭佛并不能剥夺民间的佛教信仰。事实也是如此,每次灭佛之后,都伴随着佛教的再次复兴,而复兴的民间基础就是这种民间佛教信仰。
第六,探讨居士佛教的组织形式。
居士阶层并没有自己严格的组织形式,居士林这样的居士活动团体是在1918年才在上海出现的。历史上组织表现,作者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依附于佛教僧团,二是结社的形式。
居士团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道安僧团,在道安僧团中,既有出家的僧侣,也有在家的居士,形成了以僧团为中心的居士团体,道安既是僧团的精神领袖,也是居士的归依对象,这就形成了中国居士佛教和僧团佛教的基本关系模式,即“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乃至俱荣俱衰”(第139页),这既是中国居士佛教的一大特色,也显示了居士佛教的护法特点。稍后,慧远僧团在庐山也发展出当时中国佛教最大的居士团体,随慧远发愿期生西方的123位息心之士,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居士,其《发愿文》就是居士刘遗民受慧远之命而撰的。隋唐时期,居士团体往往又依附于禅宗僧团,在许多丛林,以禅师为中心吸引着大批居士,其中不乏名居士,许多重要的碑文就是由居士撰写。这种依附性的居士组织形式反映了僧团佛教的高度发展至少涉及两个条件:一是有固定的修行场所,二是以得道高僧为领袖。
另一种组织形式和民间结社相联系。作者认为,刘遗民等人在庐山立誓,是有资料记载的第一次居士佛教的结社。居士结社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邑社,二是法社,属于“寺院的外围组织。”(270)南北朝结社以造像为主要活动,隋唐以义学和斋会为主。明清、近代结社或居士佛教团体的名称则有居士林、净业社、功德林、念佛会、莲社等。
第八,揭示中国居士的学问特色。
中国居士的学问结构,知识阶层一般都是内外兼通,内通佛学,外通儒道等学,同时,有许多居士还精通梵文。这些特点,有助于他们在中国本土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印度佛教,推进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能在融合的视角下处理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居士佛学的基本理论表现为三教关系论、心性论等。
第九,使有些史料的历史作用更清晰化。
在一般的佛教史中,对有些重要的史料,要么没有提及,要么语焉不详,而潘著能够对此多加关注并用重点发掘,作出独特的评价。这些史料包括牟子的《理惑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和《喻道论》、郄超的《奉法要》、周顒的《三宗论》、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梁肃的《天台止观统例》、李翱的《复性书》、李师政的《内德论》、张商英的《护法论》、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等等。
比如说,对《理惑论》,作者认为这部早期中国居士佛教的理论著作“成为居士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第66页)。因为后世中国佛教与本土文化争论的问题大体不出《理惑论》中讨论的问题,即夷夏关系、忠孝观念、形神关系等。如何处理中印文化的冲突,后世佛教也基本上采取了《理惑论》中的融合论模式,“既保持着佛教的某些特征,又主动适应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第66页)。
对于《喻道论》,作者认为是东晋居士关于儒释关系的代表性论文,其反映的思想成为后世居士佛教的思想基础。
对于《奉法要》,作者通过阐述其思想内容反映其历史作用,这些内容包括居士佛教五戒、十善、三斋、六斋等基本戒律和修行规范、因果报应论、儒释一致说。
对于已佚失的《三宗论》,作者从吉藏等人的著述中梳理其基本思想,并认为周颙受僧肇启发而著此论,说明“居士佛教对于佛理把握的信心日强,哲学思辨的能力也在提高。”(第249页)这对儒释都有益。
对《内德论》,作者认为它的理论价值要高于护法作用,它从理论高度对三教关系的评价,“试图把居士佛教运动引向纵深。”(第328页)有其积极的意义。
对于《新华严经论》,作者认为其核心是东方智慧论,反映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居士对佛教的认识方法。
对《天台止观统例》和《复性书》,作者突出其儒释心性会通论。
第十,突出了居士佛教的历史作用。
作者实际上从两个方面谈这种作用,一是积极的作用,二是实际上的消极作用。积极的作用既体现为知识阶层的居士通过种种方式对于佛教文化、信仰的传播和推动之功,特别是通过对经典的阐述、对教义的新解来实现这种作用。又体现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作用,比如以杨文会及其居士团体为代表的近代居士佛教,实际上代表着当时佛教义学的最高水平。但作者同时也批评了以明清以来四大道场为代表的香火道场中的居士佛教对于佛教义学的障碍作用。
总体而论,潘著《中国居士佛教史》是相当成功的对于此类专题研究的奠基之作,但是由于其“史”的体裁之限,作者的一些和“论”相关的内容,比如一些结论性意见没有得到显现。如果作者将此类的思考放在前言部分,也是一种处理方式的选择。
就此论题,引起笔者关于佛教的社会伦理问题的一点思考。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断受到批评,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社会伦理方面的,认为佛教不忠不孝,无父无君。其实佛教也一直在申明其大忠大孝,甚至比儒教更讲忠孝。既是大忠大孝,就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外在形式。问题是,中国佛教实际上的“行在小乘”,使有人很难认同其申辩。如果在信仰生活的体制上有所创新,则是一种解决方案。居士佛教正是这一方案。居士沟通了僧界和俗界、出家和在家、神圣和世俗。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能尽出家的某些责任,又能尽在家的各种职责。中国佛教重视居士佛教,实际上也在追求一种实现佛教社会伦理的有效的体制形式。
-
《中国居士佛教史》的学术特点
来源:大菩文化发布时间:2010-01-01编辑:果信 责任编辑:李蕴雨
-
专题推荐